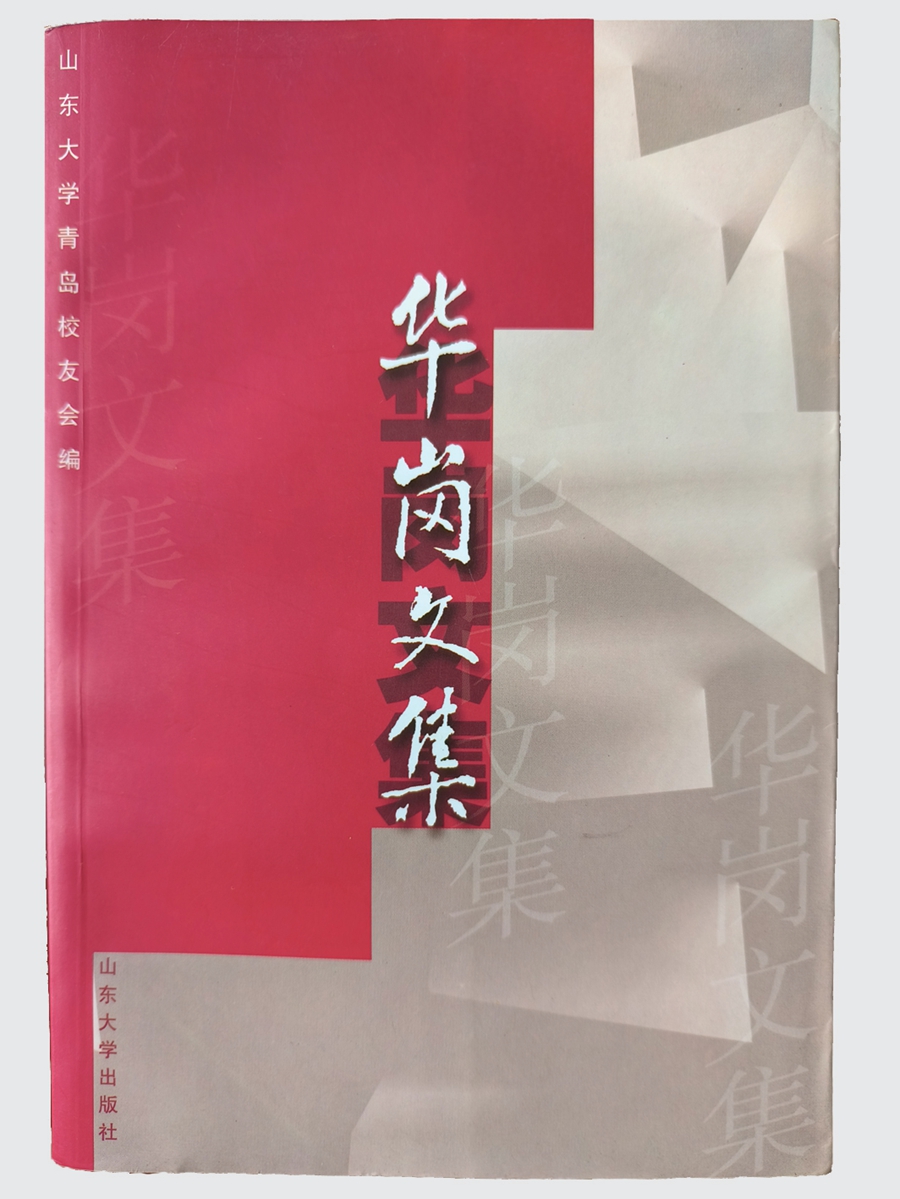
初相识
罗竹风(1911—1996),山东平度人,中国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在全国解放以前,罗竹风并不认识华岗,只知道他是一位学者,从事多学科的研究。华岗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艰苦卓绝,几十年如一日。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罗竹风以首席军代表的身份,带领十几位同志接管山东大学。下半年,山大招收新生,增聘教授,开设新课程,当时接管的军管会只有十几位同志,又是从四面八方临时凑拢来的,面对山大原有的文、理、工、农、医5个学院,再加上许多附属单位,如医院、护士学校、工厂、农场等,人少事多,忙不过来。
正在这紧张的时候,华岗从香港乘最末一班轮船到了青岛,住在迎宾馆(交际处)。华岗本是应党中央之邀由香港赶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轮船抵达上海之后,由于吴淞口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靠岸,因而转道停靠青岛大港码头。军管会主任向明通知罗竹风前往探望,罗竹风带领高剑秋和张惠同志一起拜访华岗。这样,他们就相识了。罗竹风简要汇报了山大接管后的一般情况,征求华岗对山大工作的意见,希望他多加指导。
从此以后,华岗与罗竹风不断见面,多次交换过意见。华岗曾表示:如果不去北京,新学年开始时,可以讲授《社会发展史》这门新课。华岗到青岛后,政协、中苏友协的工作顿时活跃起来。他做了不少政治报告和学术报告,例如讲解“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等,内容丰富新颖,深受广大听众所欢迎。
共同在山大的时光
华岗最后终于没有去北京,留在了青岛。他如约开始给全校教职学员开设《社会发展史》这门政治大课。此外,还在中文系开了一门新课“鲁迅研究”,这门课是分一个一个专题讲授。后来山大的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几位教授都对鲁迅有专门研究,这和华岗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当时,山大文学院是文史混合,华岗大力支持文、史分开,主张单独成立历史系。历史系成立后,为了加强师资力量,系主任杨向奎建议聘请顾颉刚、童书业、赵俪生等人任教授,顾先生因交通困难以及其他原因没有到校,童、赵两位先生在开学前都来了。鉴于以往中国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对内是以汉民族为主,对外又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山大新成立的历史系就想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加强少数民族史讲授,一方面加强对亚洲周边国家的研究;同时开设了“苏联史”和“美国史”。这是中国综合性大学第一次设置“美国史”这门课程。特别聘请黄绍湘开课,在当时“一面倒”(倒向前苏联)的情况下,更为难能可贵。由于师资、教材等条件的限制,有些设想虽一时难以实现,但对历史系课程配备的总体设想,还是大大突破了过去的老框框。华岗还写了《苏联外交史》,为研究外国史开辟了道路。
1950年春,经青岛军管会批准,山大召开师生代表会议采取民主选举的形式,成立校务委员会。华岗在会议上当选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行校长职权)。同时当选的五位副主任委员分别是:著名剧作家、物理学家丁西林,生物学家童第周,文史学家陆侃如,思想史学家赵纪彬和物理学家杨肇燫,罗竹风当选为教务长。会议同时决定:由高剑秋负责党务和全校的后勤工作,张惠任团委书记和校委会主任秘书。刘禹轩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秘书和团委委员,同时兼任校刊《山大生活》的总编辑。
校委会成立后,在华岗和罗竹风的倡议下,将学校的几栋建筑分别命名为“六二礼堂”“胜利楼”和“一多楼”。《文史哲》和《山大生活》相继创办,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高校自办校报和学刊的先河。
《文史哲》是没有经费的,由几位热心支持者从薪水或稿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来维持。例如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王仲荦、孙思白等都曾解囊相助。其中,华岗出钱最多。华岗曾说,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和研究,为国家多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材,而学报正是检验这种成就的标尺。“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群起仿效。”这些话,是陈毅同志在一次便宴上说的。
华岗和罗竹风都非常重视人才的延揽。来到山大不久,罗竹风特地到青岛观海二路拜访“文学研究会”时期的老作家王统照先生,请他到山大文史系任教。又聘请吕荧任中文系主任,聘请王仲荦、童书业、赵俪生、郑鹤声等学者到山大任教。山大迎来了继二十世纪30年代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除华岗、罗竹风和以上提到的几位以外,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赵纪彬、高亨、丁山、黄孝纾、陈同燮、许思源、殷孟伦、殷焕先、黄云眉、丁西林、杨肇燫、束星北、刘椽、刘遵宪、童第周、曾呈奎、方宗熙、王祖农、文圣常这样一些文史学家、语言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海洋学家加入山大,真是“群贤毕至”,盛极一时。
山大校务委员会秘书刘禹轩说:“回顾这五十年来的经历,如果有人问我哪一段最值得回味,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青岛解放和建国前后的那三年,因为那不仅是青岛人民和全国人民迎接解放和共和国诞生的共同的伟大岁月,也是我个人有幸在华岗、罗竹风两位革命前辈领导下度过的最受信任和重用,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人际关系最和谐,心情最舒畅,因而也能发挥作用和作出奉献的岁月。”罗竹风说,在山大工作的这一段时光,是最值得我怀念的,可惜时间并不长,如果能够继续干下去,那该多好呀!
山大华大合并 罗竹风离开山大
比院系调整震动更大的,是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校问题。1950年深秋,山东分局通知罗竹风去济南开会,参加的有彭康、匡亚明、张勃川等,还有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高教局局长徐平羽。第二次又增加了余修和刘宿贤。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山大和华大合并问题。为了稳妥慎重起见,决定由罗竹风陪同徐平羽到青岛,具体了解山大师生对合校的看法和意见。徐先见了华岗,分头参加了教职员和学生的座谈会,回济南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华东局、山东分局犹豫了一个多月,后才下决心合并,而以彭康主张最力。不久就成立了以彭康为首的“山大、华大迁并委员会”,山大参加的有童第周、陆侃如、刘椽、罗竹风,华大参加的有彭康、张勃川、余修、刘宿贤。华岗置身事外,这时政务院、教育部把他请到北京去了。
1951年暑假,山大、华大迁并业已就绪,原来接管山大的一批干部几乎都调离了。8月间,罗竹风接到山东分局转来华东局的调令,于是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准备启程。当时华岗正在上海,行前他留下一封信给罗竹风,希望罗暂时不要走,要求把罗留在山大继续工作,等他到华东局去办交涉,因为罗对山大的情况比较熟悉,对今后工作有利。但最终,罗竹风还是离开了山大。
1953年冬,罗竹风回乡奔父丧,路经青岛,去华岗家探望。夜深沉,两人相对,无限依恋。罗竹风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和华岗相见,竟成永别。
1980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华岗彻底平反,决定由山东省委主持、山东大学筹备,在济南召开华岗同志追悼会。罗竹风得知华岗早已病逝,北望云天,缅怀既往,悲痛不已!
因夫人张秀珩病重,罗竹风不能北上亲自参加华岗的追悼会。他委托华岗同志治丧委员会主任吴富恒代办三件事:一、以罗竹风夫妇的名义送个花圈;二、代表全家向谈滨若及其子女表示诚挚的问候;三、悼词如能抄写最好,宣读也可。
追悼会当天,在山东大学,许多人站在罗竹风纪念华岗悼词前,久久不愿离去。
绵长的怀念
1986年华岗学术研究会在浙江龙游成立,罗竹风任顾问,并参加成立仪式。1988年,山大召开华岗学术研究会,1993年山大青岛校友会举办华岗诞辰90周年纪念,罗竹风千里迢迢赴会。山大老学生向阳动手写《华岗传》,罗竹风给予鼓励,在写作过程中和出版方面遇到困难时,罗竹风都设法帮助解决。
1993年4月,罗竹风到济南开会,后又去青岛,虽未摔跤,腰却直不起来,医生误诊为扭伤,还进行推拿治疗。8月,因罗竹风行走不便,《汉语大词典》工委会会议安排在青岛召开。会议结束后,罗竹风要去南京开教学会议,女儿罗黛娃执意要他回家,他们就先回了上海。第二天,罗竹风住进了华东医院,当山大校友会提出准备给罗竹风写传记和成立罗竹风思想研究会时,他断然拒绝,并建议出版《华岗文集》。他在给老朋友刘禹轩的回信中写道:
关于写传记和成立思想研究会问题,于里同志主张最力,您也赞同,并愿出力,高情厚谊,我都铭记在心。但考虑再三,恐怕以不办为妙……
我是庸人,打杂而已,绝不想争一日短长。现已耄耋之年,离群索居,与草木同朽可也。务请诸位不必向我脸上贴金,幸莫大焉。接周忠雅信,似乎更加张扬了,还想联合上海社联、山东大学共同发起,并准备5月份在青岛开会研究。我回信时亦坚决谢绝,并提出最好能千方百计编辑出版《华岗文集》,这事曲风官同志和您的信中都提到过,我十分赞同,并认为是当务之急。关于《华岗文集》,我初步考虑,不妨是成立编委会或编辑组,吸收各有关方面热心人士参加,众志成城,共襄义举。可否考虑,除已出版的专著之外,一般搜集单篇文章。向阳写的《华岗传》已有附录,可仔细核对,还有哪些遗漏,资料以完备为佳。如果《文集》应以多取胜,如果《文选》应减少篇幅,求精为上。这事应由山大青岛校友会为主,曲风官、吕慧娟、吕家乡和您最好参加,此外还有谈滨若也应请她过问。向阳因编写《华岗传》,了解情况颇多,也是很理想的对象。对华校长多做点好事和实事,现在办点事真不容易,如能尽心尽力把《华岗文集》筹划出版,我们尽了一份心意,我认为这是我们所应尽的责任,华老在九泉之下,亦必欣慰而含笑。对于后辈也是一份宝贵财富。
1998年8月《华岗文集》,由山东大学出资,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编写,编辑组共搜集到华岗同志1924年到1955年发表在国内报刊上的文稿162篇,约83万字。《华岗文集》从中选出53篇,文集的许多思路是按照罗竹风指导意见进行编写的,但他没有看到该书的出版发行。
罗竹风在山大两年多的时间,和华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两人志同道合,骨子里都具有那种刚正不阿、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性格。华岗夫人谈滨若在《忆罗老对华岗的情谊》一文中写道:
罗老曾说,无产阶级应是最讲人情的,一个党员干部,有什么理由能忘记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呢?罗老待我的老伴华岗同志的关怀爱护,几十年来,完全是一往情深,使我深深感激,难以忘却。1972年老华在狱中病故,罗老听说后十分悲痛,在他的一言半语中,责备自己无能为力,未能为帮助老华改变处境而感有愧,而他当时也尚未解放,这是何等的阶级情谊啊!
华老走了已半个多世纪了,罗老也走了28年了,我相信,华老、罗老他们一定含笑相逢在天国,仍在一起谈论学问,研究着工作,就像他们在山大共事时的那段时光一样。
(作者系青年文史学者,著《罗竹风传略》)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4年第26期第7版。